1974年,在新疆七个星千佛洞附近,几个工人挖出了一张神秘的卷宗。
上面的文字,如同天书一般,没有人能看得懂。
根据卷宗出土的地点,人们推测,卷宗上的文字,应该是失传千年的吐火罗文。
而全世界能读懂这种古老文字的人,不超过30个。
让谁去破译这些卷宗呢?人们想到了我国唯一的吐火罗文大师——季羡林。
![图片[1]-我以为的都是我以为的成语,季羡林:都以为我是闷老头,其实我一生放纵爱自由-蛙蛙资源网](https://img1.wawazy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7/20230714011425301.jpeg?imageMogr2/thumbnail/700x/format/webp/blur/1x0/quality/90)
当人们把卷宗,递到季羡林面前时,73岁的季羡林,喜出望外。
他发现上面的文字,正是自己得心应手的吐火罗文。
不过,当时的卷宗破损严重,页序还是混乱的。
季羡林足足用了17年的时间,才破译了全部残卷。
1998年,季羡林整理的《弥勒会见记》正式出版,震惊了中外语言学界。
人们一致认为,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吐火罗文研究。
很多人甚至不敢相信,如此浩大的工作,居然是由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,独自完成。
一时间,赞誉纷至沓来。
人们把季羡林称为“学界泰斗”、“国学大师”、“民国大家”……
在外人看来,季羡林满身光环,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学者。
但季羡林却说:
“桂冠一摘,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。身上的泡沫洗掉了,露出真面目,皆大欢喜。”
![图片[2]-我以为的都是我以为的成语,季羡林:都以为我是闷老头,其实我一生放纵爱自由-蛙蛙资源网](https://img1.wawazy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7/20230714011427443.jpeg?imageMogr2/thumbnail/700x/format/webp/blur/1x0/quality/90)
坦坦荡荡做人
学生时代的季羡林,很喜欢写日记。
日记里有几句话,至今看来,仍让人忍俊不禁:
“早晨忽考法文,结果一塌糊涂,真是岂有此理。”
“早晨躺在被窝里,只是不愿意起。”
“我以为老叶(老师)不上班,他却去了,我没去,不知放了些什么屁。”
“看清华对附中女子篮球赛。说实话,看女人打篮球,其实不是去看篮球,是在看大腿。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,只看半场而返。”
毫无顾忌的话语,洋溢着青春少年特有的轻狂和幽默。
![图片[3]-我以为的都是我以为的成语,季羡林:都以为我是闷老头,其实我一生放纵爱自由-蛙蛙资源网](https://img1.wawazy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7/20230714011429178.jpeg?imageMogr2/thumbnail/700x/format/webp/blur/1x0/quality/90)
长大后,季羡林把年轻时写的东西,编撰成了《清华园日记》。
编辑建议他,把那些“毁形象”的口水话删掉。
可季羡林歪头想想,没同意:
“这些话是不是要删掉呢?我考虑了一下,决定不删。
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,今天不是圣人,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。
我要把自己活脱脱地,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”
言语之中,自是一番“大英雄能本色,真名士自风流”的磊落胸襟。
季羡林曾说,自己的人生信条,是“假话全不说,真话不全说。”
本着这样的信条,季老无论在什么场合,都净讲大实话。
有一次公开采访,白岩松问季羡林:
“先生的文字,到现在有八百多万字了吧?”
季羡林挠挠头:“哎呀,那里边水分也不少。”
北大校庆时,杨澜问季羡林:为什么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,回到中国?
季羡林回答:“钱多。当时一个副教授五十元,一个正教授八十元,而一石米才两元。薪水和物价实在悬殊,所以选择回国。”
95岁高龄时,有人询问季老的健康状况,他照样语出惊人:
“我的身体还可以,唯一的变化就是头发没有了,真是无法无天。”
因为学术成就显著,季羡林晚年时,被别人贴上了三大标签:国学大师、学界泰斗、国宝。
结果季羡林一听,差点拍案而起:
“岂不折煞老身!我连‘国学小师’都不够,遑论‘大师’!”
他忙忙地写了一篇文章澄清,并且昭告天下:我不过是一介平民,恳请摘下我的“大师”桂冠。
古往今来,有多少人费尽心思,打造“大师”、“行家”的人设,巴不得别人往自个儿脸上贴金。
但季羡林偏不,他撕下所有标签,向世界展现出自己最真性情的一面。
就像鬼谷子说的:
“知世故而不世故,历圆滑而弥天真;善自嘲而不嘲人,处江湖而远江湖。”
拥有一颗自在平常心的人,心中始终保留着一方诚挚热烈的天地。
任凭外界的声音如何喧哗,他们总能遵循本心,做回自己。
![图片[4]-我以为的都是我以为的成语,季羡林:都以为我是闷老头,其实我一生放纵爱自由-蛙蛙资源网](https://img1.wawazy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7/20230714011431817.jpeg?imageMogr2/thumbnail/700x/format/webp/blur/1x0/quality/90)
不拘一格治学
虽然是公认的国学泰斗,但季羡林却是一位“偏才”。
他考清华的时候,数学只有4分,全凭写得一手好文章,才被破格录取。
但让人大跌眼镜的,是在填志愿的时候,季羡林居然填了数学系。
他说:“你们不是觉得我数学不好吗?不就是因为我考了4分吗?我就想报数学系,证明我可以学好!”
要不是清华数学系以入学成绩太低为由,拒绝了季羡林,他可能就真的成为一位数学家了。
没读成数学系,季羡林只能读了德语系。
毕业后,他留学去了德国。
![图片[5]-我以为的都是我以为的成语,季羡林:都以为我是闷老头,其实我一生放纵爱自由-蛙蛙资源网](https://img1.wawazy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7/20230714011435945.jpeg?imageMogr2/thumbnail/700x/format/webp/blur/1x0/quality/90)
寻常的留学生,留学时都会选一些和中文有关的学科,减轻学业负担。
但季羡林不走寻常路,他选了难度最高的几门学科,其中包括印度学、斯拉夫语言文学、梵文、巴利文、俄文,以及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的吐火罗文。
这些语言都非常复杂,所以季羡林常说“我是在拼命学”。
他给自己定了学习的三条准则:
“第一,要学古代曾经给人类带来过荣光的语言;
第二,要学中国很少或者没有人掌握的语言;
第三,不投机取巧,关于中文的题目,一概不做。”
时值二战期间,德国战火纷飞,季羡林学习条件十分恶劣。
大部分时间里,他只能待在研究所看资料,上头飞机轰轰,肚子里饥肠雷鸣,可他却守着一堆书,看得乐此不疲。
别人笑他是不是走火入魔了,他说:
“此中情趣,非外人所能理解。”
1946年,季羡林终于回到祖国,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。
学生回忆,他每天4点就会起床,家里的灯,永远是校园里亮得最早的一盏。
季羡林曾在日记中写到:
“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。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,或能有所发现。”
本着这样的想法,季羡林每天起早贪黑,研究史料,把眼睛熬红过无数次。
后来特殊时期,季羡林被污名成“印度贱民”,被发配去看守宿舍。
即使是这样的情况,他也顶着巨大压力,完成了300万字的译作《罗摩衍那》,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立下不朽丰碑。
季羡林的学生黄宝林曾评价老师:
“越是难的东西,他越敢搞。”
季羡林自己也承认:
“甘做十年冷板凳,文章不说一句空。”
“一个人干什么事,都要有点坚韧不拔、锲而不舍,没有这个劲儿,我看是一事无成。”
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,在这位老人的世界里倾盆而下,但他心中那股不服输的心气儿,始终没有被浇灭。
也正是凭借这样求新求变的毅力,他不断地超越自我,最终到达了更开阔的远方。
![图片[6]-我以为的都是我以为的成语,季羡林:都以为我是闷老头,其实我一生放纵爱自由-蛙蛙资源网](https://img1.wawazy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7/20230714011438938.jpeg?imageMogr2/thumbnail/700x/format/webp/blur/1x0/quality/90)
不拘小节做事
1978年,季羡林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。
此时的他,已经著作等身,在学界享有盛名。
尽管如此,他待人依然亲和友善,没有一点架子。
有一年北大新生报到,有位新生因为行李太多,不方便办手续,便请求一位“老校工”帮看行李。
没想到他办完手续回来,已是正午,“老校工”还站在毒日头底下,守着大大小小的包裹。
这位新生对“老校工”感激涕零,他觉得自己遇到了好人。
直到几天后,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“老校工”发言,才震惊地发现,他竟是副校长季羡林。
和季羡林并称“燕园三老”的张中行,曾评价季老“为人朴厚。”
意思是,季老为人质朴诚厚,有时做一些事,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身份。
有一次,有位学生邀请季羡林参加学术研讨会,季羡林答应了。
可会议快开始时,却出现了意外。
季老家里的人,因为不知道季羡林还在家,出门时把他反锁在了里面。
季羡林心急如焚,为了按时到会,他竟然从家里翻窗户到了外面。
当时的季羡林已经80岁高龄,身子骨不好,差点摔折了腿,后来还是被人搀着,一瘸一拐地参加会议的。
在场的学生,看到季先生瘦弱的身影,都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除了对学生一诺千金,季羡林对普通老百姓,也十分友善。
当时北京有个掏粪工人,喜欢收集书画,还打算办书画展。
为了能吸引观众,他想找个名人题匾额,可是他找遍了那些稍有名气的书画家,都被拒绝了。
这时有人向他提议:不如去找找北大的季羡林吧。
于是,这名掏粪工人敲开了季羡林家的大门。
没想到,季老听闻他的来意,不仅爽快地题了匾额,而且还送了他一本自己的书。
这让掏粪工人非常感动,后来每年过年,他都会去季老家拜年。
而季老也会热情地请他喝茶,一起谈天说地。
季老说:
“他是掏粪工人,还自己卖书,搞了个图书馆,这个图书馆对每个人都开放的。
我对这个人非常崇拜,他不容易呀,所以后来,我也捐给他一些书。”
言语中满是欣赏,没有一点的看不起。
别林斯基说:“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,都是淳朴而谦逊的。”
越是精神高贵的人,越是懂得保持一颗平常心。
他们不会因为身居高位,对身份不如自己的人颐指气使;也不会因为功成名就,对寻常的百姓心存歧视。
无论社会地位如何,他们始终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,真诚地与人相处,温暖地拥抱世界。
一如季老,一生宠辱不惊、仁厚谦和,给一个时代,留下了闪光的背影。
![图片[7]-我以为的都是我以为的成语,季羡林:都以为我是闷老头,其实我一生放纵爱自由-蛙蛙资源网](https://img1.wawazy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7/20230714011440827.jpeg?imageMogr2/thumbnail/700x/format/webp/blur/1x0/quality/90)
2006年,季羡林被评为“感动中国”十大人物,颁奖词里这么写道:
智者永,忍者寿,长者随心所欲。
曾经的红衣少年,如今的白发先生,留得十年寒窗苦,牛棚杂忆密辛多。
心有良知璞玉,笔下道德文章。
一介布衣,言有物,行有格,贫贱不移,宠辱不惊。
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,他把心汇入传统,把心留在东方。
先生一生,治学之广博,为人之磊落,让人油然生敬。
哪怕离开我们已有13年,但在无数人的记忆里,他依然笑着,鲜活着,亲切、温暖又明亮。
我们怀念一个人,往往不是因为他获得了多大的成就,而是因为我们希望从他人生的态度里,照见一个什么样的自己。
如今谈起季羡林,我们想到的,更多是他幽默中带着豁达、温和却不乏坚忍的品格。
也正是这样的操守,让他一生不为虚名所缚,不被世俗所扰,活得诚挚、热烈而坦荡。
正如陶渊明所说:
“纵化大浪中,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,无复独多虑。”
人的一生,能够保持内心的通透,活出真性情出来,就是最高级的自由。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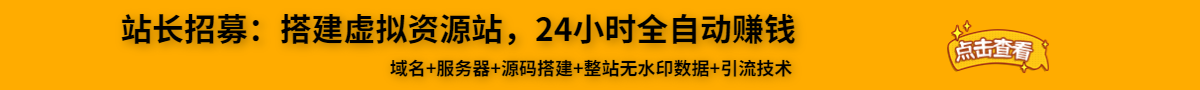


暂无评论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