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6月15日,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兰先生去世,享年64岁。
在小生行中能自己组班挂头牌的,迄今为止,京剧史上只有叶盛兰一人。他被公认为当代京剧小生的首席演员、“叶派”小生的创始人。
叶盛兰先生的天赋太好了,身段,脸型,五官真是样样合乎传统小生的理想:不高不矮,和旦角配戏,身量刚好,身材匀称,五官精致,举手投足都透着高贵气。叶盛兰扮武将壮武健爽,英气逼人,演文生清秀飘逸,富有书卷气。

叶先生祖籍在杏花春雨的江南,成长在风霜凛冽的北国,江南的水气与北国的长风同时融入了他的气质,外表兼具北雄南秀。面庞白皙,两道剑眉通鼻梁,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。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,竟如深潭静水,潋滟袭人。小生奇才,百年盛兰;菊坛翘楚,叹为观止。
1957年6月5日,戏曲界在北京召开整风座谈会。在座谈会上,叶盛兰第一个发言,他说,梅兰芳虽是中国京剧院院长,但实际上是有职无权,党政干部独揽大权,不懂装懂;京剧院的矛盾重重,工作一团糟。他说:中国京剧院剧目是照着延安的《三打祝家庄》的路子搞,有一个剧种唱《白毛女》就行了,不能叫所有剧种都唱《白毛女》。

在座谈会上把一肚子意见都说出的叶盛兰感觉很爽,会后,他到叶盛长家小憩,感慨地说:“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。”
他哪里知道,悲剧正在向他走来。
三天后,6月8日,社论《这是为什么?》发表,“反右派”运动拉开了大幕。由于在戏曲座谈会上的“放炮”,叶盛兰很快成了中国戏曲界仅次于张伯驹、吴祖光的右派分子,提出他是章伯钧伸向中国京剧界的“罪恶黑手”。

批判叶盛兰的大会,每次都是组织规模盛大,有四五百人参加。从梅兰芳、欧阳予倩往下数,京剧名伶几乎无一缺席,其中杜近芳女士的发言尤甚。
在叶盛兰先生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,杜近芳还是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知道是谁的小姑娘。杜近芳进了中国京剧院,能遇上叶盛兰,那是她的造化。从此,杜近芳的表演因有“中国第一小生”的同台、配合与提携,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、新的层面,新的境界。世事难料,如果不建立一所国家级的中国京剧院,他与她不会在一起;如果他不参加这个国家级京剧院,他与她不会在一起;如果他不是小生,她不是旦角,他与她也不会在一起。

但是,他与她在一起了,而且是几十年地在一起——一起在中国京剧院唱戏,一起唱生旦戏,一起唱才子佳人戏。他演吕布的话,她就是貂蝉;她演白娘子的话,他就是许仙;她演李香君,他就是侯朝宗;她演陈妙常,他就是潘必正;他演梁山伯,她就是祝英台。总之在古代题材的戏里,他们是相爱的一对。即使在现代戏《白毛女》里,他们也还是相爱的一对,一个演喜儿,一个扮大春。其实,他们之间的纠葛也像一本大戏,“大戏”里有深深的情,也有多多的恨。

自身条件很不错的杜近芳非常努力,力求在舞台上能与他楚汉对峙、旗鼓相当。杜近芳遇到表演艺术上的问题,也多向“四叔”(即叶盛兰)请教。于是,杜近芳迅速蹿红。同行都说,是叶四爷(盛兰)培养了她,对这样的评价,那时的她,也没站出来否认这个说法。与中国第一小生长期搭档,哪个旦角演员不羡慕,连霸气十足的言慧珠都动心。
平素他与她也很亲密,俩人能说心里话,这种亲密,同行也认可。一九五四年,组织上动员杜近芳加入共青团。她也很想入团,可又还拿不定主意,遂向叶盛兰讨教。叶盛兰听了,就撇嘴摇头。说:“你要入团?那么,将来连你的婚姻自由都没有了。”

一九五五年,中国京剧院到欧洲演出。一路上,叶盛兰对洋玩意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到了捷克,他提出要买羊毛衬衫,那时,没几个人知道啥叫羊毛衬衫。他的理由是“怕演员们晚上着凉”,希望组织能考虑一人买一件。到了瑞士,他提出要买瑞士表,还要求表商打折,再打折。他对杜近芳说:“你看人家,路灯没明线,小汽车真多,真漂亮。一路上的景致多美。美得我都不愿睡觉,愿意看这些景色。咱们祖国多咱才能赶上人家这样呐!”
在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上,杜近芳把叶盛兰平素对她的谈话内容,揭了个“底儿掉”。她的发言洋洋洒洒数千言。全文共分四个方面:一、在思想上,右派分子叶盛兰是一贯煽动我和党对立;二、在政治上,右派分子叶盛兰想尽办法拉我上他的贼船;三、在艺术上,右派分子叶盛兰对我实施暴力统治;四、在生活上,右派分子叶盛兰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……发言的结尾处,她义正辞严道:“我从各方面揭穿了‘是叶盛兰培养了杜近芳’的弥天大谎,并证实了右派分子叶盛兰怎样从政治到艺术毁灭杜近芳,已经是铁证如山!”
杜近芳处于激昂状态,说得生龙活虎;叶盛兰陷入精神混乱,听得心惊胆战。
据叶家的后代说,叶盛兰先生每次从批斗会上回到家里,什么话也不说,就把自己关进卧室。继而,就听见他在里面跟喊嗓子一样,用小生念白的声音大喊:“我是谁?”“谁敢惹我!”“在上海的时候,谁敢惹我?”“我成阶下囚啦!”

叶盛兰先生终于听到了死神将到的脚步声,弥留之际,他拉着长子叶蓬的手说:“我的病,还是因为一九五七年的茬儿(即事儿)。”
据吴祖光先生回忆,文化部的一位中层领导曾在病榻前告诉他“右派改正”的事,昏昏沉沉的叶盛兰听见了吗?吴祖光说:“那时,他已经衰弱到连面部表情都没有了。”
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,他走了,带着光耀,带着屈辱。

在叶盛兰先生告别仪式上,杜近芳女士用凄迷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死者,哭成了泪人。仪式完毕,她死死抓住缓缓移动的灵床,不让逝者归去,身子几乎拖倒在地。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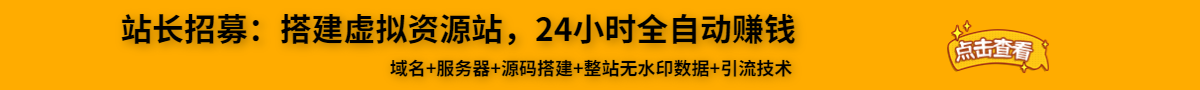


暂无评论内容